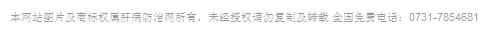安放在西藏喇嘛头部的电极,用以检测大脑活动
利维坦按:科瑞娜·阿拉米罗,一个普通的姑娘,由于脑部的一个肿瘤,已经影响到了她的语言中枢。在过去几年中,新技术能使人们看到思维、感情和行为的缘起,并以此让我们了解大脑的本质和它所产生的心灵。作者JamesShreeve专事科学写作多年,详细报道了科瑞娜大脑与意识的神奇关联,以及更多富有价值的患者大脑研究。
---------------------------------
文/JamesShreeve
译/srrsh
古埃及的人们对大脑认识甚少,他们在死去的头人埋葬前,通过鼻子将其脑浆舀出。他们相信意识仍在其心脏中,这也是亚里士多德和中世纪的思想家们的观点。即使是在人们对思想在头部形成达到共识的时期,他们也认为是大脑中的脑室产生思维,在那里有着一些朝生暮死的小精灵回旋其中。直到年,哲学家亨利·摩尔还嘲笑大脑“没有什么容纳思想的能力,不过是一堆肥肉凝乳而已”。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自信地认为,思想意识和大脑这个物质性的东西。笛卡尔主义的“二元论”对西方科学的影响力持续了几个世纪,虽然当今的科学家都反对此观点,但对许多人来说,他们仍相信心灵上个有魔力的超越一切的东西。
一个当代的笛卡尔主义者托马斯·威利斯——他也被尊为神经病学之父——首先提出,大脑不仅是思维所处,不同部位的大脑还掌管着特定的认知功能。在十九世纪初期,颅相学把这种见解推到了极致,并认为某个人的个性倾向可以从了解他的头部凸起推断,因为那部分特别发达的脑组织把颅骨推得凸了出来。颅相学家们还把那些处死的罪犯头部铸成模型,作为比较颅相的参考,以发现那些特别的凸起与犯罪行为相关。
即使是在当时,这也是十分荒谬的伪科学,颅相学仍自称它有超凡的先见之明。特别是在前十年,技术的发展,能使人们对大脑进行功能分析,从而能确定大脑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特定功能。例如,你记住一个电话号码的“神经地址”是与你记住一张脸不在同一地方,回忆一个著名的面孔与记住你的最好的朋友所需的神经环路完全不同。
然而,大脑认知功能并非想地图上的某个小镇一样,有那么确定的位置,并由该固定的那点来完成。某个特定的思维活动需要一系列复杂的神经网络和环路来完成,这需要大脑其它各部分在各种程度上的交互活动——这并像机械装置的某个零件功能那么单纯,而更像交响乐队中的各个乐器,其音高、音量、共鸣效果等,组合在一起的最终效果,才能形成完美的音乐。
科瑞娜的大脑
科瑞娜·阿拉米罗以右侧卧位躺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中心的手术台上,在她的脸颊下枕着一个枕头,头架将她的头牢靠地固定于手术台上。和她说话的是一个有着深棕色眼睛,浓密的眉毛和圆圆的笑脸的女医生助手,她大概还不到三十岁。
在外科消毒隔离幕的另一侧,两个外科医生正在紧张地在科瑞娜的大脑上工作着,她的大脑看起来好像珍珠一样泛着光芒,并随着心跳的节奏有规律地搏动着。在大脑的表面,如蜘蛛网般细细的小动脉把鲜红的血液输送到外科医生紧盯着的那块区域:左侧额叶语言中枢。紧邻其旁,就是一块深红、边界不清的肿瘤,好像一团黑暗的乌云,向她的语言中枢袭来。外科医生需要把肿瘤切掉,但又不能影响科瑞娜的语言功能。为此,他们需要科瑞娜在手术中保持清醒。外科小组先用麻醉镇静药让科瑞娜入睡,做开颅手术。在切开颅骨,打开硬脑膜后,外科医生可以看见她的大脑了,此处,再没有痛觉感受器,因此她不会再有丝毫疼痛了。
“亲爱的,醒来吧。”在消毒幕另一侧的医生对科瑞娜说,“都还不错,你能说话吗?”科瑞娜的嘴唇动了一下,她正努力从麻醉中清醒过来。
“嗨,”她轻声说。
深红色的肿瘤长在科瑞娜脑子里,即使是外行也能一眼就看出来。那肿瘤旁边就是正常的大脑,总共应该有3磅(1.4公斤),主要由脂质和蛋白质构成,有如凝乳一样洁白富有弹性。
科瑞娜的大脑真漂亮,比任何东西都美丽,甚至比她本人还美。它让科瑞娜感受美,感知自我,认识自然。但是这样的物质是怎么成就心灵的?这一堆“肉”怎么让她听懂医生的问话,并能正确地回答?通过什么样的复杂的电生化机制使她产生这样的想法:希望手术能顺利进行,或者对她的两个孩子担忧?她是怎么从记忆中找出半个小时前她母亲紧紧地握住她的手的场景,或者二十年前在小店门口的停车场的情形?这些都不是什么新问题,在过去几年中,新技术能使人们看到思维、感情和行为的缘起,并以此让我们了解大脑的本质和它所产生的心灵。
打开科瑞娜的颅腔,让我们看到了长期以来人们所期望弄清楚的心灵之源的物体。在额叶靠近她的肿瘤那部分脑区域称为Broca氏区(第一语言中枢),这命名是为纪念19世纪法国解剖学家保尔·布罗卡,他第一个提出明确的证据——所有的思维过程,特别是认知功能,都是脑中某一个特定的区域执行的。
在研究了中风患者的神经功能后,布罗卡确定了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个区域。在年,布罗卡遇到一个绰号为“唐”的病人,因为“唐”就是这个21岁的病人所能唯一发出的声音。当唐死后,尸检显示他的左侧额叶有一个约高尔夫球大小的软化灶,这个软化灶是几年前的中风所致的后果。
又过了几年,德国神经病学家卡尔·维尼克确定了位置更靠后面,在左侧颞叶的第二语言中枢。维尼克氏区受损的病人可以说话,但不能理解语言的含义,他们说的“话”也只是一堆毫无意义的声音。
直到最近,受过损伤的大脑仍是研究正常认知功能的最好研究对象。一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士兵,因为子弹击中了他头后部,因此使他产生了视野缺损,这与他的视觉皮层损伤是相对应的。某个中风病人能看到鼻子,眼睛和嘴巴,但不能把它们组合成脸。这说明主管面部识别的那部分神经因中风而受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神经外科医生怀尔德·潘菲尔德,在对癫痫病人进行清醒手术时,用电极直接刺激大脑皮层的不同地点,他发现身体的每个部位都相应地在对侧的大脑半球有主管区域,可以像画地图一样描绘出这一条状范围。例如,刺激左侧大脑半球的运动皮层,病人的右脚就会有相应的反应,同样地,刺激右侧相应的区域,左脚也会有反应。刺激皮层的其它区域还可能引发味觉,对儿童时期的生动回忆,或者记起一段已经在很久之前就遗忘了的旋律。
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那二位外科医生正准备把潘菲尔德的技术用于确定科瑞娜的Broca氏区。他们的定位已经在差不多的范围了,但在取出肿瘤之前,他们必须通过检查科瑞娜的语言能力来确认她的语言中枢的准确位置。因为科瑞娜能说两种不同的语言,这需要比其他人更精准的确定语言功能区:她的英语和西班牙语的神经功能区可能相邻,但由于她从小就说两种语言,因此这两个功能区也有可能互相重叠。神经心理学家苏珊·布克哈默正在消毒隔离幕帐后与科瑞娜交谈,从一叠卡片中抽出一张图片给科瑞娜看。同时,手术医生廖敏妃用电极触碰科瑞娜的大脑,发出轻微的电刺激。科瑞娜没有任何感觉,只是在某一特定位置,其神经功能可能暂时受到抑制。
“这是什么?”布克哈默问,科瑞娜无力地看了一眼图片。
“萨克斯管(英语)。”她轻声回答。
“好。”布克哈默说,然后再换了一张卡片。
电极已经碰到了科瑞娜的语言中枢,廖敏妃把电极向一旁移动了一点。
“这一张呢?”
“独角兽(英语)。”
“很好,‘这个怎么样?’(西班牙语)”
“‘家。’(西班牙语)”
“‘这个怎么样?’(西班牙语)”
科瑞娜略微踌躇了一下,“自行车?”(西班牙语)她说。但那张图片不是自行车,而是一对鹿角。当科瑞娜出错或努力去辨认图片中的简单物体时,外科医生就可以判断是否已经碰到了重要的神经,就像贴“即时贴”一样,他们把这些区域用无菌的小纸片标识出来。
迄今为止,这都是标准的常规手术过程(廖敏妃已经做了多例这样的手术了,他母亲死于乳腺癌脑转移)。但是今天对科瑞娜的皮层功能定位有着特殊的意义。今天,有许多人进手术室,已经超过了正常观摩人数的二倍。那些人是来这里试用一种术中“内源性信号光成像技术(OIS)”,这种技术是UCLA的ArtherToga和AndrewCannestra(他也是廖敏妃的外科助手)开发的。
天花板的吊杆上固定着一个特殊的摄像机,它正对着科瑞娜的额叶,当她说出卡片上图画的名称或回答简单的问题时(杯子是什么颜色?哪种动物会“汪汪”叫?),摄像机记录下她脑表明反射光线的微小变化。这种变化表示脑血流增加,间接地表示着认知活动所处区域。
当科瑞娜回答“绿色”,“狗”时,她的Broca氏区及其附近区域的神经活动情况被摄像机拍下来,并传送到房间一角的显示器上,图像也立即被传送到楼上UCLA实验室神经影像的超级计算机上,在那里,储存着一万个病人的多幅图像,如同这不断扩张的宇宙中的某个星系一样,科瑞娜的图像也是丰富的人脑信息研究中的一例。
“就好象每个人都面容都不一样,每个人都大脑都是不同的。”Toga说,他是神经影像实验室主任,今天也来观摩手术。“但是,通过研究上几千人的图像,我们可能从中得到些结果,弄清楚大脑是怎么回事。”
UCLA的脑图谱是用一种开创性的新技术——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来完成的。如同OIS一样,功能磁共振成像检测脑血流量作为间接了解认知活动的参数。虽然功能磁共振成像不是那么精确,但它是完全无创伤的,因此,这种方法不仅用于科瑞娜这样的外科病人,也可用于任何可以接受磁共振检查的人。这种技术已经用于检查抑郁症、难语症、精神分裂症以及其它神经系统疾病的病人,以了解其神经活动情况。还有成百上千人接受了这种技术检查,用于探索各种脑功能状态,从移动手指到回忆一个熟悉的面孔、面对一个道德难题、体验性高潮、比较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的味道等。
这一新的科学告诉我们,在28岁的科瑞娜大脑里,怎样产生了28岁年龄时应有的思维。说到大脑的生长发育,科瑞娜出生于SantaPaula,这是位于洛杉矶北面大约50英里(80.5公里)的一个农场,出生过程顺利。实际上,她在母体内的九个月对她的神经系统发育来说,才是一场大戏。
在受孕后四周,将要变成科瑞娜的胚胎每分钟产生50万个神经元。在后来的几周,这些细胞迁移到了脑部,这地点是由遗传和与周围的神经元交互作用决定的。在他母亲的第二和第三孕期,神经元互相伸出了触须,形成了突触——神经之间的联系——每秒可达万次。在她出生前三个月时,科瑞娜拥有了她所能有的最多的脑细胞:过于密集的联系。这时的神经元数量远远超过了她作为一个婴儿所需要,甚至超过了她作为成年人所需要的。
然后,在她出生前一周,这个过程逆转了。一组组神经元互相竞争,并建立彼此建立专门功能的神经环路。那些没有建立联系的神经元凋亡了,此过程称为“神经达尔文主义”。
这些有功能的神经已经开始对其要面对的时间做好了准备。在出生时,她已经能从陌生人中分辨出自己母亲的声音,熟悉在母体中听见过的摇篮曲,甚至可能对她妈妈做的墨西哥食品有了喜好,因为她从羊水中已经尝过了。最后一个完全发育的感觉是视力。即便如此,她也能在出生后第二天就能认出她妈妈的脸庞。
在其后的18个月中,科瑞娜是个学习机。婴儿的大脑汲取着她感觉器官所能接触到的所有刺激。
“看起来好像她们就坐在那里盯着啥东西,”伦敦大学Birkbeck的大脑和认知发展中心的MarkJohnson说,“正是从此开始,孩子们开始汲取信息。”当科瑞娜开始体验这个全新的世界时,反复接受刺激的神经环路不断强化突触联系,而那些静止休眠的神经萎缩了。例如,在出生时,她能听出世上所有语言的各种发音,而当西班牙语的音调(后来是英语)充斥在她的耳朵里后,她的大脑语言中枢对这些声音更敏感,而对其它的声音,如阿拉伯语、斯瓦西里语等,就不敏感了。
在前额叶皮层,即大约在她的额部到耳际处的范围,科瑞娜的自我意识开始出现在这部分的神经组织里。在此区功能尚未完全发育前,孩子们会去试图擦掉他在镜子里映像上的“小孩脸上的脏东西”,而不明白镜子里的映像是他自己,更不会擦他自己的脸了。
当科学家在研究高级认知功能时,他们发现人类的“自我意识”在大脑中不像汽车的汽化器一样,固定于某个特定区域,也不像花朵开放一样,在某个时间同时发育成熟。它的功能位置和成熟过程可能与大脑中各个不同的区域和神经环路有关,按各种特定的感受器和各个神经环路发育的时期而定。
因此,当科瑞娜在三岁前在镜子里看到她自己时,她还不知道,还需要一年后,才能明白那就是她自己。在路易斯安那州拉法耶特大学的DanielPovinelli和他的同事的研究中,他们给小孩玩游戏的过程拍录像,然后悄悄地把一张大胶纸贴在他们的头发上。几分钟后给这些孩子们放录像时,三岁以上的孩子大都能到头上把胶纸撕掉,表明他们懂得录像里的那个“我”就是现在的自己,而小于三岁的就毫无这个概念。
但三岁时的科瑞娜是不会记得头上有胶纸的。她的最早的记忆是和妈妈一起到商店去挑选一件有蕾丝花边的粉红色裙子,那令她多么激动啊!那时她四岁。更早的事情她记不起来了,因为她的海马回——主管长期记忆的大脑边缘系统的一部分——还没有发育成熟。
但那不是说更早的记忆就不存在于科瑞娜的大脑中。因为在她二岁时,她父亲就离她们母女而去,她不记得他父亲酗酒并殴打她妈妈,但与那相关的情绪可能储存于她的杏仁核,那是在出生后早期就有功能的大脑边缘系统的另一个结构。高度情绪化的记忆铭刻于杏仁核中,虽然大脑没有意识到,但这仍在影响着我们下意识的行为和感受。
在我们的青少年时期,大脑不同的部位以各个不同的速度和方式发育成熟。当然,在早期科瑞娜的大脑像学习机器一样工作时,对其正确的塑形非常重要。但最近报道,根据UCLA和马里兰州Bethesda的国立精神健康学院多年来对儿童的影像学研究,大脑灰质在青春期前有出生后的第二次爆发性增长。
作为一个典型的女孩,科瑞娜的大脑皮层在11岁时最厚(男孩还要在晚一年半以后)。在这次快速生长之后的10年内,大脑灰质逐渐变薄,直到最近才完成此过程(28岁)。最先完成这一过程的是那些有关最基本功能的,如感觉中枢和运动中枢,那是在大脑的前部,其次就是那些主管空间定向和语言中枢,分别在顶叶和颞叶。
最后成熟的部分是前额叶皮层,那也就是所谓的执行中枢:我们做出决策,比较各种情况和选择,计划未来,以及保持我们的行为举止处于常态之中。
“执行中枢直到25岁时才达到成人水平。”国立精神健康研究院的JayGiedd说,他也是神经影像研究科学家里的带头人。“在青春期,你有成人的热情、性欲、活力和情感,但很好地驾驭它们还要等到很久以后。”因此,青少年似乎都毫无判断力,不能控制冲动——这都不足为奇。“我们18岁能参加投票,”Giedd说,“还能合法地拿驾照。但你要到25岁才能去租车,也就是说,从解剖学角度看大脑,能租车的年龄才到成熟的时候。”
灰质成熟,并不代表神经的高级精神发育终止。即使在现在,科瑞娜的大脑仍在不断地发展。前一个十年神经科学研究的主题至于就是对大脑的发展和塑形的研究,特别是在成年后对其自身的不断改造和再加工。识读盲文的人,其感觉运动皮层(大脑处理触觉的中枢)的体积显著增大,特别是主管右手食指区域。而小提琴家们则是左手手指的感觉运动皮层增大,因其需要琴颈上跑来跑去地演奏各个音符,而仅是管理持弓的右手皮层区域则相对较小。
“十年前,大多数神经科学工作者把大脑看作计算机,在其生长发育早期获得了确定的功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MichaelMerzenich说,他是研究脑功能塑形性的先驱者,“但现在我们知道,大脑中人的一生中不断地对自己改良。”
但是,当大脑的自我塑造功能在老年时衰退前,仍然可以令成人大脑不断学习新的技能。根据Merzenich实验室的初步报告,即使在60~70岁的老人,通过专门的学习仍能使其已经衰退的记忆功能恢复青春。这种可塑性没有止境,除非某一个重要中枢,例如Broca氏区,被中风或肿瘤所破坏,病人就不会激活现有处于静默状态的神经环路,以恢复其功能。
现在我们回到科瑞娜今天的手术中来,在她的左侧额叶中,鸡蛋大小的肿瘤已经在她大脑里破坏了保持她的性情、组织能力和主观能动性的神经环路。幸运的是,大脑对于这些高级功能尚有内在的冗余系统,因此她的家人并没有发现她的个性改变:右侧大脑的对应区域担负了左侧大脑损害所造成的功能欠缺。
但是,肿瘤仍需尽快切除。研究人员已经完成了对她大脑功能的内源性信号光成像处理,以及另外一种红外线扫描技术的实验。在吊杆上摄像头已经缩了回去。
此时的手术室,除了手术组,其他的人都已经离去。科瑞娜已经非常疲劳了,但她还要保持清醒,坚持一会儿。廖敏妃医生用电刀分开肿瘤和科瑞娜的Broca区大脑之间的边界。在消毒隔离幕的另一边,布克哈默医生拿出更多的卡片给科瑞娜看。
“这是什么?门?很好。(英语)”
“这个怎么样?(西班牙语)”
手术刀越切越深,口罩上,廖敏妃的目光也越来越紧张。她必须完全切除肿瘤,但又不能伤到一点点脑神经,否则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到肿瘤的边界上切除干净了后,科瑞娜终于可以入睡了,因为其后的操作不需要她再保持清醒的反应了。
“她现在好吗?”廖敏妃医生问。
“非常好,”布克哈默答道,“完全没问题。”
“好,”廖敏妃医生说,“让她睡觉吧。”麻醉师从静脉输液中,给科瑞娜加了点什么药,我走过去面对着她的脸。
“科瑞娜,”在她快要闭上眼睛入睡时,我对她说,“你的大脑真漂亮。”
她轻轻地微笑着说,“谢谢!”--------------------------------
转载请注明:http://www.uzngq.com/zlzd/4863.html